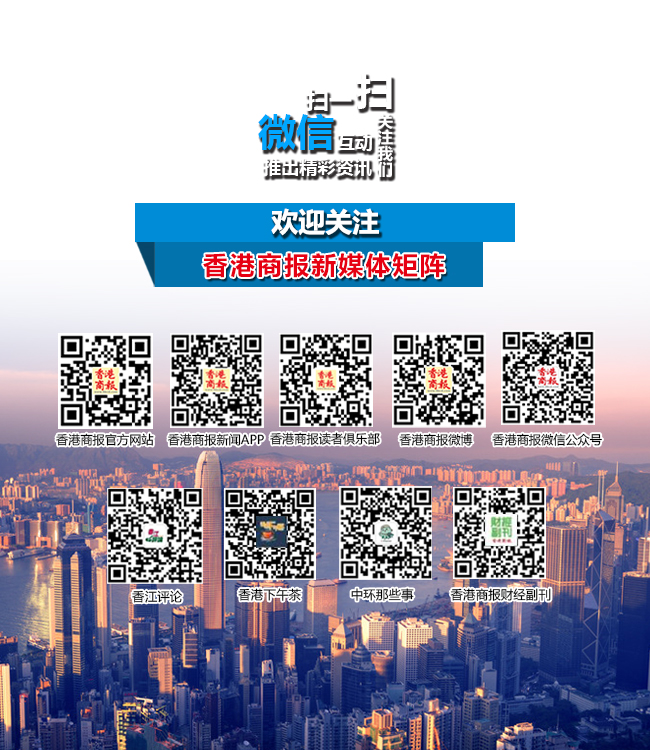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翠入深山》(国画) 宋陆京 作
●杨健
饶公走了,走得平静,走得安详,也走得有点突然。
饶公家客厅墙上的挂历上2月9日这一栏,至今清楚写着“杨健 4 pm.”几个字。就在几天前我与饶公家属约好,9日下午四点陪同我办王志民主任去探望饶公,提前给他拜年,未料他6日凌晨竟溘然仙逝,令人唏嘘慨叹不已。
2月28日,饶宗颐先生追思送别仪式和大殓仪式在香港殡仪馆隆重举行,各界人士500多人在此与饶公沉痛告别。灵堂迎面墙上悬挂着一副挽联:“宗风不磨意,颐真自在心”,正中摆放着饶公遗像,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彩照——深蓝西服,条纹围巾,清癯的面庞,专注的眼神,和蔼的微笑,如今已成永恒。
一
我在广东工作时,饶公的名字就如雷贯耳。饶公是广东潮州人,家乡人说起饶公,无不引以为傲;国内学术界、文化界人士提到“饶宗颐”三个字更是推崇备至、称颂有加。
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位集大成者,其卓绝学术造诣和杰出艺术成就广受膜拜,有人将其与钱钟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南饶北季”;有人将之与王国维合尊为“前王后饶”(20世纪汉学前半部看王观堂,后半部看饶选堂)。
由于年事已高,近年饶公深居简出。我因工作关系,有幸每年去探望饶公,从他身上感悟学习令人崇敬的卓越学识、高洁品格和家国情怀。
第一次见饶公是2013年来港工作不久,我去看望他,约在他家附近酒家一起午餐。那年,他96岁,虽走路有些颤颤巍巍,但身板挺直,双目有神,双手有力。他在与我握手时,使劲攥紧我的手掌,并左右摇动,连连加力,然后孩子般得意地问我手劲如何,我赞其力道惊人、可敌后生,他开心地笑了。
落座后,饶公握住我的手近五分钟没有松开,问我何时来的香港、气候适不适应、饮食习不习惯,我一一作答。在座的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小女婿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港大原副校长李焯芬。
作为饶公的学生,李焯芬十分敬重饶公,从学校退休后,他的很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饶公、服务饶公。李焯芬介绍说,饶公学识广博,其研究涉及国学的几乎所有门类,包括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史学、考古学、目录学、楚辞学、金石学、礼乐学、宗教学、方志学、古典文学、中国艺术史、中外关系学等,近年饶公主要整理过去研究成果,同时带领团队继续对一些疑难问题展开研究。
饶公女婿邓伟雄说,他每日仍抽时间写字作画,作画以画荷为主,他的腕力不错,画巨幅荷花时,十尺长的荷梗仍可画笔轻挥,一贯到底,亭亭秀直,遒劲有力。
饶公小女儿饶清芬一边细心地用剪刀将饶公爱吃的菜肴剪成碎粒,方便饶公咀嚼吞咽,一边告诉我,饶公生活很有规律,每日晨6时起床,到楼下花园散步,上午9时多再小睡一下,然后看书、研究等,晚9时左右一定宽衣就寝。
有人做过统计,饶公治学80余载,共出版学术专著70多种,发表论文近千篇,刊行诗文集10余种、书画集数十种,可谓著述宏富、学艺双携。
我一直心有疑问,一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就算每日宵分废寝,也难成如此道山学海;常说隔行如隔山,就算着力杂学旁收,也少有这般学艺双成。
这位旷世奇才是怎样“炼成”的呢?
二
2014年8月初,我去饶公家探望,提前祝贺饶公生日。从他家离开后,我约李焯芬教授在附近喝茶,刚落座,我就向李教授请教心中疑问。他回答了三个字:“求知欲!”接着给我讲了三个饶公治学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学无国界”,李教授说话轻声慢语,但有板有眼,抑扬顿挫。他说,大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饶公在港大从教时得知6万余册敦煌文献世纪初被人“拿”走了,其中13000多卷到了英国,5700多卷到了法国。饶公下决心研究这批文献,10多年时间里,他经常抛家别女远赴欧洲,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敦煌文献,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月,写了大批研究论文。以后,为寻找流落海外的其他敦煌文献和中文古籍,他的足迹踏遍五大洲。饶公最喜穷根究底,为了搞清一个问题,总是不分古今中外,寻找各方资料求证。为此他除了熟练掌握英语外,还学了法语﹑日语﹑德语等,甚至研究了中古梵文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从此,他的国学研究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
“第二个故事叫学无边界”,李教授说起饶公的事如数家珍。他说,饶公的研究从来不给自己设置领域的限制,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弄懂什么问题,因而能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真正的大学问家。他举了一个例子,大约20年前,在一次讨论中,他曾向饶公请教《史记》“禹迁三苗于三危”中“三危”的含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1000多年来大多认为夏禹王迁苗人至三危,“三危”指敦煌三危山。但始终有人质疑,三危山不大,是沙漠中一座光秃秃的荒山,几十万苗人迁到那里,怎么生存?饶公听后觉得有趣,说去研究一下。过了几个月,饶公拿出一篇文章,竟是关于这个问题求证的论文。他通过查找商代资料,发现了甲骨文中有关“危方”的记载,由此得出三危并非指敦煌三危山,而是危方,即广袤的西部。“方”指方国,是指中国古代被称为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居住区以外的周边地区。为何加“三”?这是古汉语的一种习惯称呼,如陕西被称为三秦大地,湖南被称为三湘大地。三危就是西部地区。由于饶老精通甲骨文,故而能将之延伸到历史研究领域,取得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李教授告诉我,这篇论文后来收进了饶公所著《西南文化创世纪》一书,可以送一本给我看。第二天他就让人送了书来,我仔细读了论文,其扎实的史料、认真的论证、严谨的推理令人折服。
“第三个故事叫学无止境”,李教授说,饶公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饶公总说做学问应该退而不休,他的研究成果有三分之二是退休后完成的。其中他最为关注考古新发现,或通过新出土文物定证过往的研究,或从中推展新研究、探寻新成果。2002年6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惊现战国至秦汉时期古城遗址,填补了国内秦代古城考古空白,特别是其中1号井出土的3.7万余枚秦简,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价值可与殷墟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等媲美。那年饶公已经85岁了,听说里耶有重大出土发现后十分兴奋,很想过去看看。湖南考古部门得知后,派人专程把整理好的秦简内容送来给他看。他马上投入研究,据此写出多篇论文。前几年他看到南昌西汉海昏侯考古发现的报道,同样兴趣浓厚,获悉考古队队长来港参加活动,马上与之见面。
听完三个故事,我恍然大悟,想起饶公回首往事时发过的一句感慨:“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
三
此后,我又多次探望饶公或出席与他相关的重要活动。
2014年11月2日,中山大学在香港大学举办嘉誉礼,将该校设立的“陈寅恪奖”颁赠予饶宗颐,这是饶公继荣获国家文化部“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国家文物局“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别贡献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荆勋章后获得的又一崇高荣誉。我应邀出席了仪式,并问候饶公。
2015年2月10日,我陪时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赴香港大学看望饶公,向他致以新春问候,并赠送由深圳大学美术系主任刘声宇创作的饶宗颐肖像油画。饶公很喜欢这幅油画,连说:“画得好、画得好!”
2016年12月3日,全球22个从事饶学研究的机构在香港成立“饶学联汇”,饶公出席了成立仪式。我在成立仪式的致辞中说,饶公博古通今、通文达艺、学贯中西、腹载五车,被誉为“一代通儒”“国学大师”,可谓实至名归。
去年春节前,我去饶公家探望,向他问候新年。在座的李焯芬教授告知,饶公将于6月亲赴巴黎出席“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展”。以百岁高龄万里迢迢赴法国?我忧心饶公身体能否承受路途颠簸。李教授说,饶公身体没有问题。他又解释道,饶公与法国很有渊源,从1958年开始就被法国国家科学中心、法国高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邀请到巴黎参与研究和讲学,并曾出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客座教授,许多法国乃至欧洲著名的汉学家都是饶公的学生。饶公还先后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国际汉学界最高荣誉“汉学儒林特赏”、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建院125年来第一个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衔、法国文化部文化艺术军官勋章等荣誉。这次法国多家机构力邀他前往展示其艺术成果,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饶公女儿饶清芬补充说,父亲对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很重视,很想去故地走走,并看看自己的法国学生们。为了确保路途顺利,有关机构特意包了一架中型飞机,将4个头等舱座位都安排给饶公使用,其中两个拆了改装成床,另外两个改成宽敞的座位供他坐着休息。飞行途中父亲一直十分兴奋,不时用手指轻击桌面作弹琴状,口中念念有词。后来我得到消息,饶公这次法国之行非常成功。
8月初,我再赴饶公家看望,贺他百岁华诞。
饶公家住跑马地,透过客厅阳台门,跑马场一览无遗。客厅正面墙上挂着饶公手书“如莲华在水”的一块横匾,这是饶公最喜爱的一句话。饶公一生甘于寂寞、远离浮华,心无旁骛、物我两忘,心境平和、心灵祥和,把全部身心放在了做学问上;他对国家和民族怀有深厚情感,坚决拥护“一国两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热心捐助灾区重建,无私捐献精品力作。他的高洁品格正如莲华在水,不染淤泥。
饶公坐在沙发上,着一件灰色外套,银白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明澈的眼睛透过金边眼镜专注地看着我说话。他的听力已明显衰退,表达也有些含糊不清,但他的思维依旧清晰依然敏锐。当我与他交谈时,其女饶清芬不停地用潮州话在他耳边大声翻译。他显然听清了我的问候,我祝他鹤寿绵长、寿比南山,他连连说:“老得不像话了”;我赞他博学广识、人格高洁,他不断摇头:“不敢当,不敢当!”我向饶清芬询问饶公身体近况,她说饶公口味好,睡眠好。我称赞她夫妇对饶公的悉心照顾,并说,饶公在学问的厚度和深度上创造了奇迹,我们由衷祝愿他在生命的长度上同样创造奇迹。
此时,饶公静静地望着前方,像一个腼腆乖巧的孩子。他没有再说话,但我相信,他的思维一刻也没有停止,或许他在想他那些没有完成的研究,或许他在琢磨某个未曾定证的悬疑,或许他在牵挂一个新的考古发现,或许他在构思一幅新的画作。可以肯定,只要生命不息,饶公的研究和创作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我想起了季羡林先生生前发自肺腑的一句话:“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巨星陨落,九州同悲。今年2月6日上午和2月8日晚,我先后两次陪同王志民主任赶赴饶公家中吊唁及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对饶公逝世的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还是那个客厅,还是那张沙发,还是那块横匾,但斯人已去,音容永诀。王志民主任与饶公交往多年,他动情地对饶公家属说,饶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践行者,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率;他的学术造诣、艺术成就和国家情怀受到广泛称赞。他是香港的骄傲,也是国家的骄傲。
大师西去,风范长存。
饶公,一路走好!
(本文作者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副主任)